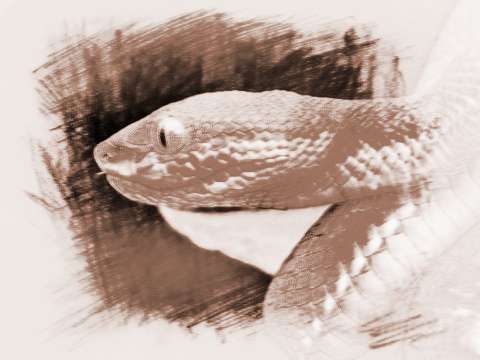《阆中作家》2024/4月刊(总第047期):中天漫道下

刊名|张炳俊 封面制作 |修守为
按
城门稳沉地关闭着,需要进出城的人要被迫绕很长的路。正对着雨神的北门由官府的正式法令关闭了。雨已过剩,这是对雨神的重要暗示。我见过别处的许多城市在干旱的时候关闭正对火神的南门,因为火神只能从这个方面进城。在干旱时期火是非常可怕的,当房屋的木料被烘烤到易燃的危险情况下(伊莎贝拉·伯德《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据说,在当时被誉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征服中国价值的书。后来,被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吸收为第一位女性会员。作为冒险家和传教士的乐园,神州包括中国内陆的城镇乡村,无一例外都成为他们镜头下的猎奇和猎物。换一个向度,散文、随笔的写作,跟照相机的摄影镜头捕捉是一样的:表达即发现。(江阳公子。本期图片摄自陕西汉中留侯庙)

目录
诗语阆中
赵逊(四川阆中) 垂钓(外二首)
范文波(四川西充)故乡的月亮(外二首)
王飞(四川阆中) 王飞的诗(组诗)
陈正清(四川阆中) 油菜花黄
王羽格(四川阆中) 赶路人
中天漫道
何家祥(四川武胜) 春暖花开古城香
黎冬梅(四川阆中) 楼下的修车店
李双(四川阆中) 老王
阿米(四川阆中) 家庭记趣
王雄(四川阆中) 老屋
鼓角轻骑
韩斌(四川阆中)在贡院广场上一愣(组章)
江阳(四川泸州)瞳孔与贡院碧梧(外五章)

阿米(四川阆中)
家庭记趣
题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快乐的家庭各有各的故事。
虚 惊
2023年7月的一个周内,是我的生日。按惯例招待一下家人和朋友同学。几桌席设在广场靠古城的一个酒店。
席间,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跑来跑去,兴奋不已。还给我和客人以水敬酒,表达祝贺和热情。
中午一时过,客人们酒足饭饱之后,主人结束了就餐,便就地安排了“吃耍一天”的喝茶打牌活动。我叫亲家母带孙女回家午休,两点过还要上学。孙女感到现场热闹喜庆,众亲友大多没有离开,她也不想走。我便上前去追她,让她回奶奶家休息。追又追不上,她边跑边说:“要睡我也在这里睡!”于是,我就交给她奶奶管,自己与亲友们准备打小麻将了。
可一转身,她奶奶却说:“怎么娃儿不见了?”
我立马开始在大厅找,还把雅间、厨房和厕所找了个遍,都不见人影。
我把这个情况说给大家。
奶奶回家去找,婆婆在附近餐厅找,随后众亲友都放下手上的牌或者水杯,在附近的楼上楼下、街里街外到处寻找,我一个搞公安的朋友甚至到一公里外我家附近找。
因女婿在外地上班没参加此次宴请,我也及时电话告知已回家午休的女儿。她叫马上报警,并及时赶过来了。见仍无踪影,她流出了少见的眼泪。随后,我与妻子陪警察去广场监控室查监控,但也没一点线索。
女儿的几个同事朋友也赶过来帮忙寻找。其中一个听说了一些情况,分析说,怎么一眨眼就失联了,应该没走远。
于是,大家又从她消失的地方地毯式地找起。
忽然,我的一个姓杜的同学在一张餐桌的桌布下面拼起的两个凳子上,发现了正酣睡的孙女。家人松了一口气,亲友们也松了一口气,慢慢地才恢复了打牌喝茶的欢声笑语。
事后,我很自责。
没认真体会那句“要睡我也要在这里睡”。至少有三层意思:我要陪爷爷过生,不想睡:想睡也在这里睡:更隐含着我不会离开这个饭厅的。我没有学过刑侦,误判了,让大伙儿也跟着虚惊一场。
可这虚惊里,包含着童心、亲情、友情!
鹦 鹉
龙年春节期间,我们把乡下年已八旬的岳母接进城,安排长住我们家一段时间。因为舅子、连襟们年后又外出奔生活。
人们常说:有一种幸福,叫上有老下有小。作为四代同堂的我们家,还是第一次。一时间,既有天伦之乐的喜气,又可能有些许的不适。
为尽快适应,也为了传播家庭文化,尤其是孝道文化,我想尽快进入角色。有一天在饭桌上,妻子对小孙女说:“从现在起,外祖祖是我们家里的成员了,而且是重要的成员。”
我接着解释道:“重要到什么程度,没有祖祖就没有婆婆,没有婆婆就没有妈妈,没有妈妈就没有你!”
第二天吃饭时,闲聊中,在机关上班的女儿又提醒她的孩子:“没有祖祖就没有婆婆,没有婆婆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你!”
过了几天,妻子在伺候她母亲时稍有点不耐烦,声音略有点儿大。
孙女听到后,对她婆婆说:“请小声一点,没有祖祖就没有你哟!“
我心里暗喜,这一系列的鹦鹉当得真好!
各找各妈
这是三月的一个周末。上午孙女去训练了一个多小时的乒乓球,回到家兴致极高地在客厅玩玩具。女儿在阳台靠厨房的洗衣台洗衣服。妻子在厨房里忙做午饭。
饭菜熟了以后,妻子在喊她母亲和孙女吃饭,我也赶紧附和着叫岳母和孙女吃饭。
忽然间,孙女丟下手中的玩具,几步就爬上楼去(我家房子是错层式),没见着她妈妈,又蹬蹬蹬地跑下楼,在保姆室看、在卫生间找,最后在阳台的洗衣台前终于找到:“妈妈,快上桌吃饭吧!”
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这是亲情的传递,也是孝顺的接力。
原来,是我孙女误会了。为什么叫了其他人吃饭,却忘了她的妈妈。也许她后来才知道,洗衣台紧挨厨房,还用得着叫吗?即使叫了,孙女也听不见。
席间,我把看到的这一切讲述给女儿,她听了感动得喉咙都有点紧似的。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找各妈,各回各家”也是人间的至爱亲情!
阿 米,实名罗玉泉,四川阆中人,机关退休人员,有散文、新闻作品在省市报刊发表。情寄山水间,乐于太极拳。

王雄(四川阆中)
老 屋
春节回到我的小山村,弟弟的新屋前面,耸立着我们的老屋。
一眼望去,曾经居住多年的老屋,南边原有的土墙已荡然无存,只有靠北边的厨房和卧室还在,却早已破烂不堪,严重倾斜,即将倒塌,院子也被长长的藤蔓所覆盖。站在裸露草丛里的柱墩石上张望,我的心情一时变得更加悲凉。
眼前,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堆黄色的墙土。
墙土的缝隙,长出一丛丛荆棘,一簇簇野草。墙土未覆盖之处,还能依稀看到早年的门框和积满臭水的猪草缸。当年曾和伙伴们一起嬉戏的院坝,已满地杂草。仅剩的两间残存木屋,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孤零而又顽强地坚守在那里。它像是在不断地向世人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弟弟给我说,老屋在他房子前面,既影响视线又有安全隐患,要不想办法推倒。我看那样的确危险,就去找了一条棉麻绳,用竹竿把绳头夺到柱子的穿梁上,叫上堂兄堂弟来帮忙。随着口号声的响起,大家一起用力拉扯然后再松劲,房顶就吱吱嘎嘎响过不停,随着我们一拉一放地来回折腾,房顶的瓦片开始坠落,整个房顶的摆动也越来越大。随着弟弟一声快跑,破败的老屋轰然倒塌,溅起的尘土久久才散去,露出了厨房里孤零零的灶台和水缸。
想起了我孩童时,母亲在灶台忙碌的身影。
与老屋相关的往事,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心情一下子失落到了冰点,而我童年的载体,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屋,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和弟弟在这里捉迷藏,抓小鸡,踢毽子,种花草。
老屋,见证了我奋斗的点滴。从懵懂少年到稚嫩的青年,求学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的夜读,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时母亲那盼儿归乡的喜悦。
老屋修建于1985年。
当时我五岁,赶上我们整个家族的四合院拆除。
四合院中所有的人家都在修新屋,其时没有砖瓦结构一说,都是请人在山上开采石条回来作地基,然后工匠师傅就用一个木匣子在石条的地基上用泥土加上竹条或木条,一层层地迭起来,工艺很像现在西藏的藏族同胞建房。记得建房时临近冬天,天天几十号工匠忙前忙后。父亲因为还要工作,建房现场几乎都是母亲在协调,而舅妈和姨妈就要负责工匠的一日三餐。因为四合院一下子拆光了,只能用稻草搭一个简易棚子供一家人临时居住。
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
早上醒来,总能看到稻草棚外白白的一层霜,脚踩上去都会吱吱响,还会脚底打滑。
那时候,也不觉得冷。早早就会爬起来,围着工匠跑来跑去,往往是在工匠师傅的吼骂声中溜掉的。工匠师傅怕伤到小孩子。只要一帮孩子一靠近,就会发出吼骂。
前前后后好像建了三个多月,一套土坯瓦房总算建好了。
染上红色油漆的木柱和风檐板,再配上用石灰粉刷过的白墙,看起来特别气派。父亲在单位上班,见识也多些,就特别把堂屋旁边的两间房子,配上了大窗户,还配上了双开玻璃窗,里面配上了有椰树及美女的热带风情窗帘。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建房,是很时髦的,很有些前卫感。我爷爷家及其他邻居家建的房子都没有窗户,连白天进去也是黑漆漆的。
房子建好后,我们兄弟也不愿意去邻居家串门了,总觉得邻居家的房子没窗户怪怪的。特别喜欢傍晚,在窗户边一边做作业,一边欣赏落日余晖的美景。还可以瞄着母亲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好把小人书藏起来。但天黑后,我们就不愿意在窗户边写作业了。总担心抬头,看见窗外有啥东西。农村没有通电,晚上的照明靠的是一盏用红岩墨水瓶改造的煤油灯。
记得煤油灯伴随着我,几乎是读完了小学。
然后,小山村才通上了电。
想想都可怕,风吹油灯摇摇晃晃……
父亲在单位工作,母亲又热情好客,家里总是客人不断。放学一路小跑回家,掀开锅盖,能看到母亲给我们留下的饭菜。父亲傍晚回家,端杯泡着茉莉花茶的搪瓷缸,在院子里和邻居闲聊。到现在对茉莉花茶的香味,也毫无抵抗力的我,完全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过阵子,就泡一泡来解一下馋。
那时候农村物质生活匮乏。
父亲在单位的缘故,孩童时的物质生活比同龄人相对要好得多。舅舅和姨妈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我和弟弟也几乎没有干过农活。顶多就是扫扫地,或帮忙割一下猪草,农忙假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假期,是真的疯玩。家里的农活,父母亲都会请邻居帮忙,完全轮不到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太了解什么季节种什么,什么季节收什么!我和弟弟没事就去田间地头,弄些野花种在院子里。什么指甲花、美人蕉、鸡冠花、菊花,甚至不知道名字的花草,我们也会弄回来。一般是种不活的,不是浇水太多了,就是太旱了。要不就是我们种的季节不对。好像种得最好的,就是在小溪边上挖回来的石菖蒲。记得挖回来种了一株,这次看到已经长成了好大的一片,郁郁葱葱开着花。特别喜欢在夏天的院子里乘凉,听着蛙鸣声,闻着花香,皎洁的月光犹如白昼。躺在簸萁里手握一把䈬扇驱蚊又避暑,望着满天繁星听着父母坐在旁边聊天,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什么时候被父母抱上床的,压根就不知道。
母亲在院子前的菜园里,种满了瓜果蔬菜。金黄色的南瓜,成串成串的四季豆,长满刺的黄瓜也逃不过我们的魔爪。摘下来用衣服擦一擦直接就塞进嘴巴的黄瓜,又解渴又解饿(不知道是嘴巴吃刁了,还是黄瓜变异了,现在是找不回儿时的那种味道)丝瓜炒了煮面条,韭菜割了包水饺,白菜砍了炒油渣,萝卜拔了炖猪肉,母亲的菜园子就是一个聚宝盆、百宝箱,啥东西都可以在里面翻出来。经常是母亲已经在捞面条了,才吩咐我跑去菜园子里掐几株葱回来调味,一点也不影响开餐。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在茁壮成长。求学,工作,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远,老屋的印象也越来越模糊。不会特意地去思念,只是偶尔会梦见。老屋一直在,我们也没有失去的心里准备。2008年汶川地震对老屋有些影响,母亲也一直在我耳边唠叨,说谁谁家又建了新屋了,谁谁家又迁到更靠近公路的地方了,说你们不回农村居住没有关系,但根在这里一定要有祖屋在才对。为了满足老人的夙愿,也不想被邻居笑话,就在另外的地方选址重建了一栋小楼,父母也搬到了新屋居住。
老屋仅仅堆放了一些柴禾及杂物,却终究是常年无人居住,又来不及修缮,就慢慢倒塌了。见证了老屋的修建,又亲手拉塌了最后一根柱子和残存的墙壁。
我感慨万端。
佑护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成人,陪伴着我们度过艰难岁月,老屋完成了使命,但永远是我的回忆和圣洁之地。
王 雄,四川阆中人,南充作家协会会员,阆中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