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丧事,老妈乔迁“新家”记

丧事,从来都是乡村社里的至大事件。那些人情世故,虽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可它刻在人们心底,千百年传承不断。
撰文 / 金何(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 秦旭东
鹧鸪天·思母
一树一花一院风,春来冬去绿香椿。花开桃木今犹在,不见去年树下人。
对望后,断归程,从此只能梦相逢。别离半面犹似笑,魂已望乡情是情。
2018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凌晨三点多,老妈走了。那天正好是她生日。此前,我写了 。
老家习俗,不兴厚葬,人去世后一般停灵三天。第一天准备各项事宜,第二天入殓凭吊,第三天下葬。下葬三天后复三,下葬三十五天后做五七,下葬一百天后百日祭。
乡村的人情世故,虽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可它刻在人们心底,千百年传承不断。尽管全国各地都在推殡葬改革,河南省前几年还掀起了平坟运动,但在老家那边,既有的丧事传统还根深蒂固。
对于死,老妈一直看得很淡,“那才是我长久的归宿,没啥,以后记得给我弄好点就中。”丧事,从来都是活人世界的事,流程繁琐可能漏洞百出,枝节横生难免引发是非。
算日子
人一断气,丧事就算正式开始。老爸是十里八乡出名的阴阳先生,过去村里死人都是来找他的,这套流程他再熟悉不过。自己妻子走了后,他心里早已纷乱如麻。“今天正是个吉日,不犯重丧,三天后就能下葬。”老爸把日子确定下来后,就给一众亲友打了电话。
给老妈把寿衣穿好后,我大伯家那边的堂哥嫂也过来了。他们站在屋门口进退两难,我不禁扭脸看了一眼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老妈。说来话长,老爸有两个大哥,当初因为照顾爷爷的事宜兄弟失和。后来各种蜚短流长,我家和大伯家矛盾扩大,很多年没有什么交集来往。
“我死了,他要来给我穿孝,你就把他给我推出去!”这话,老妈这几年说过不下十几次。但是,这种丧事临头,通常也是失和兄弟“和解”的契机。
搭草铺
棺材还在后院,明天入殓时用。我跟大表哥抬走了棺材盖子,二哥和二表哥搬了长条凳。
条凳支好,棺材盖子摆放客厅,其上放三根稻草。众人簇拥着把老妈抬到草铺上。老爸把拴了红线的一枚小钱塞入她的口中。接着,我也没看清老爸又拿了什么东西,分别往老妈的左右手里放,我接过去一份塞进了老妈的右手。从穿寿衣到现在间隔了不到十分钟,她身上的余温已经彻底散失,手心那种冷让我不寒而栗。

压纸
屋里一众小辈分都跪下了,一切收拾妥当后要“压纸”。屋里烧一点纸钱,屋门口再烧一点,最后要把一张白纸压在街门外的下水出口处。众小辈都发出了哭声,此时我却没一丝想哭的冲动,脑子里像被填充了迷茫,又像是被抽空一切后只剩迷茫。
纸烧毕,哭声也戛然而止,我搞不懂这些哥哥嫂子们为何能恰到好处地控制自己的节奏。忽然想起《水浒传》里一句话: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嚎。家乡这边在办丧事的时候也有一句老话,叫“盖活人眼”,说的就是丧礼的盛大与简朴,亲人的悲痛程度,都是做给外界看的。
“亡人”
大伯在县里居住,天亮后领二哥去给村里“亡人”磕头的任务,就交给二伯了。本来磕头要由长子,可大哥远在桂林,傍晚才能赶回来,因此根据长幼次序,就得由二哥代劳。
本族人掩埋亲人有违礼制,所以死人后丧葬事宜,都是村里的外姓人来代做。这些代劳起坟、做饭、抬棺、下葬等各种事情的人,在家乡这块被称为“亡人”。村里只要不是在外地工作的,几乎所有成年人一生里都会做好多次“亡人”。毕竟谁家都会有亲人去世,这实际就是村人之间的相互帮忙。
假如有一天,村里的一个外姓人突然向你下跪磕头,不用问,他的爹或娘肯定不在人世了。通常,村里都有几个有威望的男人做“亡人队”的头头。本族人先领孝子去给“亡人头”磕头,之后再由“亡人头”带着孝子去给各个“亡人”磕头。至于找谁来帮忙,那就看谁在家谁有空了。一般只要磕了头,没什么重要的事大家都不会拒绝帮忙。
如果父母过世,子女在村里找不到“亡人”帮忙,那说明你在村里的人品不行,是极其丢脸的事情。要由本族的长者再次带领孝子去找“亡人头”,要下礼也要道歉。即便最后“亡人”们找来了,大家伙儿也会恶心甚至刁难主家,此后主家会被当成笑话在十里八乡流传好久。
“亡人头”张叔吃早饭后过来的,他劝我爸不要太难过,家里家外这三天的事儿,他跟族里会操持好。
“亡人”们都在坟地忙活,由于去年就已经把坟建好了,所以他们现在也不用劳神费力,只需把埋葬我妈的那一半坟挖开就行。不过在开挖之前,逝者的孩子得先去挖三下土。大哥没来,二哥去报丧了,所以得我来做。
守灵
家乡这里还保留着土葬的一切流程。前些年政府曾倡导过平坟火葬,刚开始村民们还不以为然,认为是虚张声势。不过发生了几起“逝者下葬后,又被挖出来送去火葬”的极端情况后,各村村民才逐渐遵循制度去火葬。但火葬归火葬,之后的丧葬还是按照土葬的方式进行。又过了些时日,由于管得松懈,一切又回归到了原来的样子。
九点半多,两口大锅和碗筷瓢盆,抬棺用的绳索铁链,搭灵棚用的支架等货品都拿来了。大表哥把食材买回来后,剩下的事就交给“亡人”们来做了。灵堂前,一张小供桌早已摆好,香烧烛燃。香和蜡烛烧没了都得续上,不能让它断了。大表哥把老盆放在供桌前:“中午吃饭的时候把饭菜放进去一些,每顿饭放一次,到出殡那天放满就行了。”
老大家的两个女儿,也即是我堂姐来了,局促的客厅里,气氛沉默甚至有些尴尬。不过,烧纸和哭泣两个流程还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否流泪,灵堂里很快又是哭声一片。我跪在众人之间,感受到的不是悲痛,一想着这些十几年不踏入我家门的人在哭,甚至感到有一丝滑稽。
现在开始,除了上厕所,孝子基本不再出灵堂。中午的时候,二表哥先往供桌上的老盆里添了些饭菜,然后挨个给在屋里守灵的人端来了饭。我就坐在老妈的下首侧旁,想着今后她再也吃不上饭,在扒拉了一口菜后,泪如雨下。
下午吊唁者陆续增多,每来一位,孝子都得跪哭以示悲痛。因为客厅里都被亲朋占满了,茂庆叔就在阳台上支了一张桌子,写挽联、糊哀杖、做引魂幡和摇钱树。他是我本族八爷家的孩子,我们这些小辈都该叫他叔。
族里几个叔叔大爷都在,陪着我爸抽烟喝茶。看着一个个脸上像扭蛇般曲折的皱纹,我觉得时光真快。现在那些爷爷辈的已经凋零,一眨眼的功夫,轮到父亲这辈人的身上了。

傍晚八点半,大哥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还未放下背包就走到了老妈的草铺前,众亲朋围着他,老爸把蒙脸的白手巾掀开了。哭声响起,撕心裂肺。没能见娘最后一面,成了大哥永久的心结。是夜,灯火通明,各个门不关。家里人开始给第二天守灵的亲朋准备孝衣。
入殓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一。一大早,我们全部都穿上了大孝,要到明天下葬后才脱下来。一般是至亲和近门穿重孝,远门小辈,只戴孝帽即可。
入殓在下午进行。棺木放一旁,先在底部撒一层石灰,接着按北斗七星的形状放入7枚铜钱,是谓垫背。最后把一条棉被铺入棺底。
一切准备就绪后,就要请母入棺了。长子抱头,二哥站在中间,我则在老妈的脚部,过程必须一气呵成。看着自己的至亲被放入狭小逼仄的“匣子”里,谁都会悲痛无比,不过长辈们还是在一旁不断地叮嘱,“不能哭”“忍住”。有说法是入殓哭会招邪,另一说是易致病,孰对孰错,莫衷一是。
请入棺后,要往馆内添物。家乡已无厚葬一说,贵重陪葬品没有,但要填塞逝者生前的衣服,越多越好。在我看来,往棺木里塞很多衣服,就像楔子一样,是防止在抬棺过程中,尸体晃动而发生位移。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衣服都有,都是老妈生前的衣服,塞得是满满当当。
最后是擦脸。端一碗水,用棉球擦。我们兄弟三人,每人擦三次,并且每擦一次,都要象征性地喝一口水。我擦的时候,感到老妈的脸冰凉而僵硬。她躺卧在棺中,已彻底融入了另一世界。
哭丧
入殓同时,院子里的灵棚也搭好了。之所以院外也设一个灵位,是因为吊唁的时候,男性是不进屋内的,只有女客才进灵堂。而每来一个吊唁者,哭丧环节必不可少,如何才能知道有男客来呢?灵棚外放一个铁桶,每来一个吊唁者,守灵人敲一下铁桶,屋内的孝子也就知道有人来了,只需放声大哭即可。子女和侄子女们在屋内,屋外是孙子辈和族里的小辈。
我记不清从入殓后到傍晚哭了几次了,男客和女客都有,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村里的左邻右舍。有时是真的在哭,有时是恰好没有眼泪只能干嚎。老爸和族里的长辈说过,一定要哭出声来,不能小声抽泣。
所谓哭丧,一种意义是指子女亲人的哀恸,另一种说法是,子女如果不哭泣,就不能帮吊唁者破除晦气。可见哭丧是一种事务性行为,不管真哭假哭,哭出声来就行。
请乐队
乐队赶在吃晚饭的时候来了。一起来的还有老妈的小辈儿给她送的花圈。一个亡者花圈的多寡,完全看这家的亲戚有多少。不过老爸事先给各个亲戚家打了招呼,尽量别上花圈,一切从简。而且按老爸之前的意思,乐队都不打算请,花钱不说,有些乐队吹奏一些欢乐的曲子,完全没有悲伤的气氛。事实是,上个月族里的一个老人过世,乐队开场居然吹奏《小苹果》还带舞蹈,让老爸着实恼火。
“不中,不请乐队,村里人不笑话爹你,可是会笑话俺们。”二哥不同意,因为请乐队已经是丧事中不可或缺的流程。我的意见是无所谓,生前过好、活好、孝顺好才是主要的,死后所做的一切,都跟死者没有关系。不过我又能理解二哥,他常年跟村里人打交道,如果老妈的丧事不按照大众的习俗去办,人们会在他背后指指戳戳的。
在豫北乡下,婚丧事流程人们极为看重,大多数家庭的原则是:不过度铺张浪费,但该花的钱,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花,绝不能当落单者。整体来看,林州地区的丧事还不算太铺张,但奢靡的丧事不是没有,难怪某些地方一场丧事下来会使家庭返贫。
老爸最后答应请乐队,但他划了一条红线:“不能吹奏欢乐的曲子,不成体统!”
这个晚上,主要是村里的乡邻来吊唁上祭,我们在屋里是哭了一茬又一茬。在家乡,上祭品的习俗还是很农业化,并且具有北方特色。无论族人、亲戚还是乡邻,祭品都是烧饼和馒头,是谓乡亲礼。所以村里某一家办丧事,都会收到很多烧饼馒头,最后吃不完甚至坏掉。
吹奏完毕就是深夜12点多了,族人去做了宵夜,乐队和守灵人都吃了一点。“你得去把门口那张纸揭回来。”大表哥对我大哥说。老妈走后压在大门外的那张白纸,必须得在今夜,由长子揭回来,焚化。之后,从焚化那一刻开始算起一直到天明,约摸每隔半小时烧一次纸钱。一整夜,大家在聊天消磨时间。
暖房
最后一场哭丧中,我突然心生某种遗憾:要是老妈有女儿就好了。女儿不但能为老妈大声哭丧,还能在第三天的上午,到坟地去给老妈“暖房”。
老妈没有女儿,“暖房”的任务只能让大侄女代劳了。可大侄女正好是大伯家的姑娘,虽然借助于老妈的丧事,表面上两家和解了,可真要是让大姐做“暖房”这个事,人家愿意吗?老爸面有难色,二伯也不知所措。
十几年前的另一个矛盾,就是因为让他家闺女代劳我二哥喜事上的一个流程而引爆的。虽然事情的性质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因我家没有女儿,流程里需要一个女子而引起的。过去女子在乡下的地位相当低微,可在婚丧嫁娶的习俗里,恰恰有些流程,非她们不可代替。幸而老爸跟大侄女商量后,她同意去。
第三天出殡,异常忙乱。老爸还是抽空,把一个暖水瓶用金纸糊了,他说要放进墓里,让老妈喝水用。
二嫂和堂姐,拎着鏊子、柴草、两个烧饼去坟地“暖房”了。所谓“暖房”,就是下到墓室里把柴草点着,用鏊子象征性地热一热烧饼,两人各吃一口烧饼,最后把烧饼掰开分别扔到墓室的四个角落。这就等于替老妈在下面的新家开火做饭,等她到了后,这里就有烟火气了。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习俗也奇怪,既然相信人死后投胎转世去了,她又怎么会在坟墓里“安家”呢?
“暖房”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值守在墓地的“亡人”,要所谓的“开墓门”钱。这纯粹是一种善意的小玩笑,有时候主家的女方和“亡人”熟识,嬉笑起来会更恣意一些,但嬉笑之前双方却都要装得一本正经。一般也就给10块或者20块买烟的钱。
敬奉孝布
上午十点多,后家亲戚来了。先是敬奉孝布,由长媳端着孝布带领孝子们下跪敬奉。由于大嫂没来,二嫂端着孝布走在前头敬奉。就在此时,族里一个大娘突然一把夺过二嫂手里的孝布,喝令她到一边去,又拽过大哥,把孝布放到他手里。她的意思是,让大哥代替他媳妇去敬奉孝布。
这么一折腾,二嫂不干了,她觉得那个大娘在当众羞辱她。于是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诸多不是,场面极其尴尬。二伯和老爸先后站出来打圆场,都没能止住她情绪的发泄。
我忍受不了这样的场面,悲和气夹击下,扑通跪在老妈的棺木前嚎啕大哭。维系乡村关系的,是血缘和熟人,但事实上血缘里的亲情,很微妙。我没有看到是谁在拽我起来,但二嫂的诉说声停止了。
钉棺
这段插曲过后,午饭也好了。端饭进来的族人劝我们,一定要吃,不能空着肚子出殡。饭毕,是出殡前最后一个流程——钉棺。
棺材钉上那将真是永别。看着大锤长钉,我对两个忙碌的“亡人”大喊:“等下!让我瞧俺娘最后一眼吧。”
他们把盖子掀开,我看到老妈仍旧静静地躺着,所有的嘈杂、哭泣、悲痛、不和……她都不用再理会了。“亡人”们随即把盖子放回原位开始钉棺,砰砰砰的声响,就好像把钉子楔进了我的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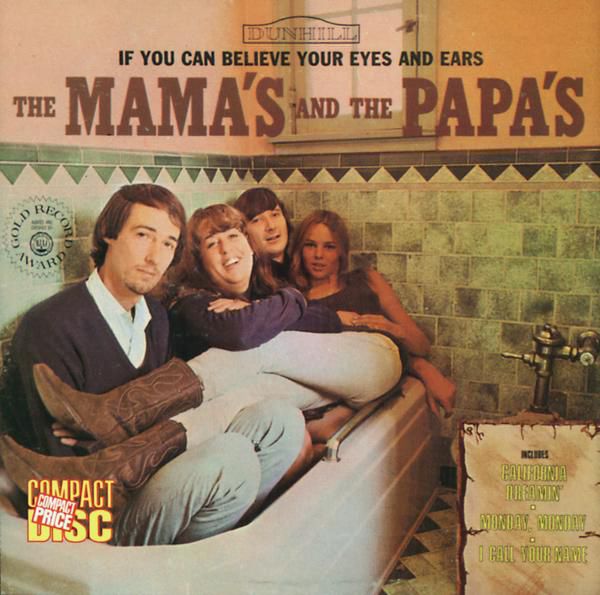
“娘,甭害怕啊!娘,躲开钉子啊!娘啊……”大哥二哥围在棺木周围大喊着。我没想到我也会哭得昏天黑地。
钉棺之后,棺材要先被扛到街门外,由于大头处沉重,哪个“亡人”扛大头,主家会额外给他50块钱,这钱直接放在棺材大头的盖子上。
摔老盆
“起!”一声喊后,三五个“亡人”扛抬着棺材,吆喝着一脚踢翻放在正门口的一小袋玉米,在嘈杂声里穿院而出。接着大哥在众人的搀扶和帮助下,先把引生罐挂在脖子上,那里面是一罐白米饭,罐口用馒头牢牢塞住。引魂幡和哀杖拿在右手,左手捧着装满饭菜祭品的“老盆”。
我恍恍惚惚的,由于双眼酸涩又半低着头,看不清谁是谁,只感到周围都是人的下半身。棺材就停放在街门外的条凳上,此刻已拴好绳索,专等摔老盆后抬棺出殡。茂庆叔过来指出摔在哪里,大哥后退几步,然后疾步上前猛地把老盆摔在棺材前头的正下方,粗糙的瓦盆应声而碎。
出殡
老妈活着的时候,我就想过,将来出殡送葬的路上哭不出来咋办?如今我真的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头,才知道之前的想法是多余的。眼睛控制泪滴的阀门好像失效了。最重要的是,一个三天前还跟我一起看电视的人,现在被装进了一个木头匣子里,要被永远地埋入地底下。埋葬的不仅仅是一个逝者,更是我和老妈的亲情和美好时光。
快到坟地的时候,“亡人”们甩开队伍,抬棺抢先到达坟头,是谓“抢葬”。大哥要下到墓室,把长明灯、梳子镜子等物品放进墓室墙壁的凹槽内。之后,“亡人”们要以绳系棺入墓。棺木安放好,大哥再次下到墓中,把暖水壶放置在棺木的旁边。最后封好墓门,再用泥巴糊住缝隙。接下来还是由长子先填三下土,之后十来个“亡人”迅速把土回填。
其后,大部分的花圈烧掉,剩下一两个盖在坟头。随风飘扬的引魂幡和摇钱树下,一座新起的坟默然而现。老妈从去世到“乔迁新居”,还不到72小时。

老妈的坟头。
回灵席
“亡人”和乐队回去之后,还要吃一顿饭。只有米饭和肉,不放任何其他菜肴,是谓回灵席。饭毕,给乐队结账,通常一两千块钱不等。村里的“亡人”,每个人也会象征性地给十几块钱。一般三天事毕,花销五六千块,若是富裕家庭,上万都不算多。
复三
安葬老妈后第三天,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只有我家还沉浸在悲痛中。重回坟地,我才发现引魂幡上只写了贾李氏而没有老妈的名字。中国式的男女不平等从生一直延续到死。

上午祭奠回来,老爸信誓旦旦地说他看到老妈回房间了,可我们都认为他那是思念过度所致。这三天我和老爸一起睡,就在老妈曾经躺的位置。
老爸忽然对我说:“只有暖水壶,没有水杯怎么喝?脸盆也忘了,这些等做五七的时候,连同衣服一并给恁娘焚化了吧。”“我想梦见恁娘。”他又说了一句。
五七
这个年过得寡淡无味,一个月转瞬即逝。
五七在坟前一定要痛哭,这样才能把五阎王的心哭软,放恁娘过关。这是老爸之前一再强调的。
五七那天清晨,我早早带着要给老妈焚化的衣服,先去了坟地。潮湿的坟头上,那张没写老妈名字的引魂幡,不知被风吹到哪里了。我之所以独自前来,是担心自己在二哥二嫂面前哭不出来。很多衣服都是化纤面料,燃烧起来很慢。大哥正月初五就走了,他电话说今天下班后也会去大街上给老妈烧点纸钱。

“五七”,二哥在坟前焚化妈的衣服。
吃午饭的时候,老爸告诉大家,邻居冯老汉在县肿瘤医院化疗,贲门癌中晚期。五天后,村里那个26岁的脑瘤患者,也走了。
“活着时间快,死了也快。”老妈生前常说。
清明
清明这时,正好老妈去世60天。两个月,已化春风映入泥。我已经开始想不起来她说话时的声音了。我知道,时间会一点点消融掉我脑子里关于她的一切。娘,等我百年后,咱们再相会吧。
运营统筹 / 迦沐梓
运营编辑 / 张建林
校对 / 阿犁





